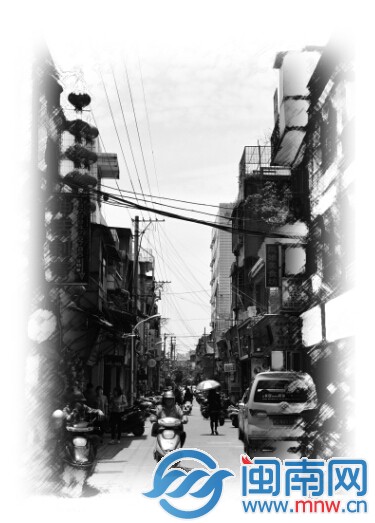 如今的花巷已無(wú)發(fā)飾店 東南網(wǎng)5月20日訊(海峽都市報(bào)記者 林永清 田米 文/圖)原來,城里的女人,也有不愛逛街的時(shí)候。只不過,那是百年前的事了! 《THE CITY OF SPRINGS》第四章就提到,那時(shí)在泉州街上幾乎看不到都市女性,只有很少數(shù)的老阿嬤,相反,那些在田里干活要挑東西到城里賣的農(nóng)村婦女,倒是經(jīng)常見到。 如今的花巷已無(wú)發(fā)飾店 英國(guó)傳教女孩安妮,對(duì)此用了“嘖嘖稱奇”來形容,顯然像她那樣在古城街道穿梭游覽的事,對(duì)于當(dāng)時(shí)的中國(guó)都市女性來說,怕是有點(diǎn)“不符合身份”了。 泉州這座千年古城,那些有著濃厚歷史印記的古街巷,狀元街、東街、打錫街、西街、花巷……每一條街巷,都有著打動(dòng)心扉的故事,而在安妮的筆下,卻別有一番風(fēng)味。 □《THE CITY OF SPRINGS》 第四章譯文 泉州,街道和商店(節(jié)選) 不大清楚這個(gè)地方的輪式交通工具,只看到腳穿草鞋的苦力悄悄地走過不平的路面。城市的喧囂聲音與英國(guó)國(guó)內(nèi)的街道噪音不同。我們聽到的是當(dāng)?shù)胤窖缘男鷩蹋憙r(jià)還價(jià)的聲音占多數(shù)。僅僅是對(duì)一些小事的討價(jià)還價(jià)的爭(zhēng)辯,對(duì)我們看起來應(yīng)該進(jìn)行友好的討論,可能現(xiàn)金的總和不過500文(一便士)。如果我們有時(shí)間等待,我們應(yīng)該看到各方最終圓滿地結(jié)算,但是我們前方的挑夫大聲地吆喝宣告我們轎子的到來,相對(duì)于路人和扛行李者,轎子有優(yōu)先通過權(quán),但是對(duì)巡境的神像人偶卻要避讓。 有時(shí)候我們會(huì)覺得我們的椅轎就要撞到大街上的行人,當(dāng)差一點(diǎn)就撞上老人時(shí)我們都屏住呼吸,然后下一分鐘我們覺得幾乎要撞上一個(gè)攤位,我們的轎夫不計(jì)后果地跑步上前,不斷地喊著,“朗一賴賴賴!” (閩南語(yǔ):“人來了,人來了,人來了!”),幸好都是有驚無(wú)險(xiǎn)。我們只記得有一次,我們的椅轎有點(diǎn)重地與一個(gè)匆匆過客撞了滿懷。 都市女性,除了少數(shù)很老的人,街上幾乎看不到城市婦女,讓人嘖嘖稱奇;但家住農(nóng)村在田里干活的婦女,經(jīng)常在泉州街頭可以看到。這些婦女形成一個(gè)群體,有較多的自由,他們放開天足,就像男人在田間地頭干活,種植水稻等工作,挑擔(dān)出入城市。他們生活艱苦,穩(wěn)扎的步態(tài),健康開闊的面龐,日曬雨淋造就紅黑的膚色,與之鮮明對(duì)比的是那些楚楚可憐、蹣跚步態(tài)、足不出戶的城市姐妹不健康的膚色。 街道兩邊的店鋪都令人充滿興趣。也許應(yīng)該要叫攤位才對(duì)吧,大部分算不上商店。早上門板取下時(shí),店主拿出各種支架和木板,從而增加了商品陳列的位置。然后,還要把沉重的木制招牌放在顯眼的地方。所有這一切都嚴(yán)重侵犯已經(jīng)十分有限的街道空間。 有一些街道是專營(yíng)同一類商品的商店。走進(jìn)那狹窄只能沿著墻根而立的街道,這里每家店鋪賣的除了筆還是筆,全都是筆。紫貂的或兔子的毛發(fā),固定在一個(gè)竹筒上,用小綹的毛做成中國(guó)的毛筆。泉州是座有文化的城市,因此筆備受歡迎。 這里是花巷,這里每家店鋪展示的都是女性用的金銀掐絲和絲綢人造花發(fā)飾。另一條街專賣男人的鞋。這些鞋子,與無(wú)處不在紅色圓頭的“碗帽”,是泉州兩個(gè)特殊的出口商品。 稍遠(yuǎn)一點(diǎn)的街道較寬,我們發(fā)現(xiàn),除碗、茶杯等外,無(wú)非都是賣陶器和瓷器的店。他們的貨物擺到街上,沒關(guān)系,中間還有一條清晰的通道,都有遵守。  王強(qiáng),黎明大學(xué)外語(yǔ)貿(mào)易與旅游學(xué)院副教授。 □翻譯志愿者 【解讀】 擁擠的街道應(yīng)是西街 稍寬的或是聚寶街 “她(安妮)描述的基本符合當(dāng)時(shí)的情況,一些場(chǎng)景我小時(shí)候還可以看到。”泉州市方志委副主任許曉松告訴海都記者,那時(shí)候泉州主要的街道除了匯成一個(gè)十字架的東西南北四條街外,還有就是聚寶街和打錫街,當(dāng)時(shí)街道也比較擁擠,安妮所描寫的大部分場(chǎng)景應(yīng)該就是在西街一帶,“一些店家開門做生意的習(xí)慣,甚至還保留至今,比如拆門板擺街邊再擺上東西的做法”。 在一張老照片里,兩排房屋錯(cuò)落有致,東西塔矗立在上方。許曉松說,“在西街的房屋多為名門望族和家廟宗祠,很有規(guī)模,卻顯得有些破敗,有些房屋甚至都倒塌了。這也從側(cè)面反映了當(dāng)時(shí)的社會(huì)狀況,民間的修復(fù)能力低,只能對(duì)房屋進(jìn)行勉強(qiáng)地修補(bǔ)”。 安妮還提到,“稍遠(yuǎn)些的街道比較寬,除碗,茶杯等外,都是賣陶器和瓷器的店”。許曉松認(rèn)為,這應(yīng)該就是在聚寶街,因?yàn)槿輰?duì)外貿(mào)易興盛,當(dāng)時(shí)這里是外國(guó)商人聚集的地方,這條街上多賣金銀珠寶、綢緞布匹、香料藥材和茶葉瓷器等。“安妮提到專賣男鞋的街,就是現(xiàn)在的帽巷,當(dāng)時(shí)都專門賣帽子和鞋子,到新中國(guó)成立初期還在,因?yàn)槊弊酉裢胍粯樱跃徒忻毕铩!?/p> 幾百米長(zhǎng)花巷 人造花發(fā)飾今再不見 安妮走在100多年前的泉州城,她看到在花巷里,每家店鋪展示的都是女性用的金銀掐絲和絲綢人造花發(fā)飾。在安妮的筆下,雖然只是簡(jiǎn)單的一句話,但我們?nèi)钥上胂螽?dāng)時(shí)花巷的場(chǎng)景。可讓人惋惜的是,如今這幾百米長(zhǎng)的巷子,能跟之前的“花”有關(guān)的,只剩下巷口保留的那兩家花圈店了。 泉州市文史專家楊清江說,花巷以前叫蒙古巷。起初,因?yàn)槟歉浇哪瞎臉浅珀?yáng)門下有重兵把守,西側(cè)有官屋,供屯駐軍兵居住,他們大部分是蒙古人和色目人,信奉伊斯蘭教,所以人們就把他們駐扎的地方的小巷叫“蒙古巷”。 “因?yàn)槿菖⒋虬鐣r(shí)喜歡插上一些花,遇上婚慶喜事,婦女的頭上也有戴花的習(xí)慣,這樣能以示吉祥;而遇喪事需綁扎花圈,做‘功德’需綁扎紙厝,祭祀先人。因此,泉州傳統(tǒng)的扎花手工一直長(zhǎng)盛不衰。”楊清江說,到了清末民初,蒙古巷那里慢慢集中了很多制作和出售手工藝花卉制品的花店,人們就將那里叫做花巷了。 “上世紀(jì)50年代還有剩幾家會(huì)做手工藝花卉制品,到了60年代后就基本都是做花圈了。”楊清江說,一些習(xí)俗在改變,市場(chǎng)需求也變了,到了現(xiàn)在,花巷也剩下兩家花圈店,但也是有著百年歷史了。 【尋地】 專賣筆的街巷 你可知它在哪? 在這章里,安妮還提到有一些街道是專營(yíng)同一類商品的商店,比如說在一狹窄只能沿著墻根而立的街道里,每家店鋪賣的全都是筆。 楊清江介紹,上世紀(jì)50年代,在南岳宮口到涂門街那一段路,曾會(huì)有比較集中賣毛筆的店鋪,但也并不是全部的店鋪都賣筆,之后那些店也都慢慢消失,但并不像安妮描寫的那般。許曉松也說,泉州是一座文城,向來重視教育,人文教育氣氛一直很濃厚,所以存在這樣一條專門賣毛筆的街道也并不為奇,只是他也不知道這條街是在哪里。 這條街,略顯神秘,如果您知道它是如今的什么地方請(qǐng)與我聯(lián)系。 |